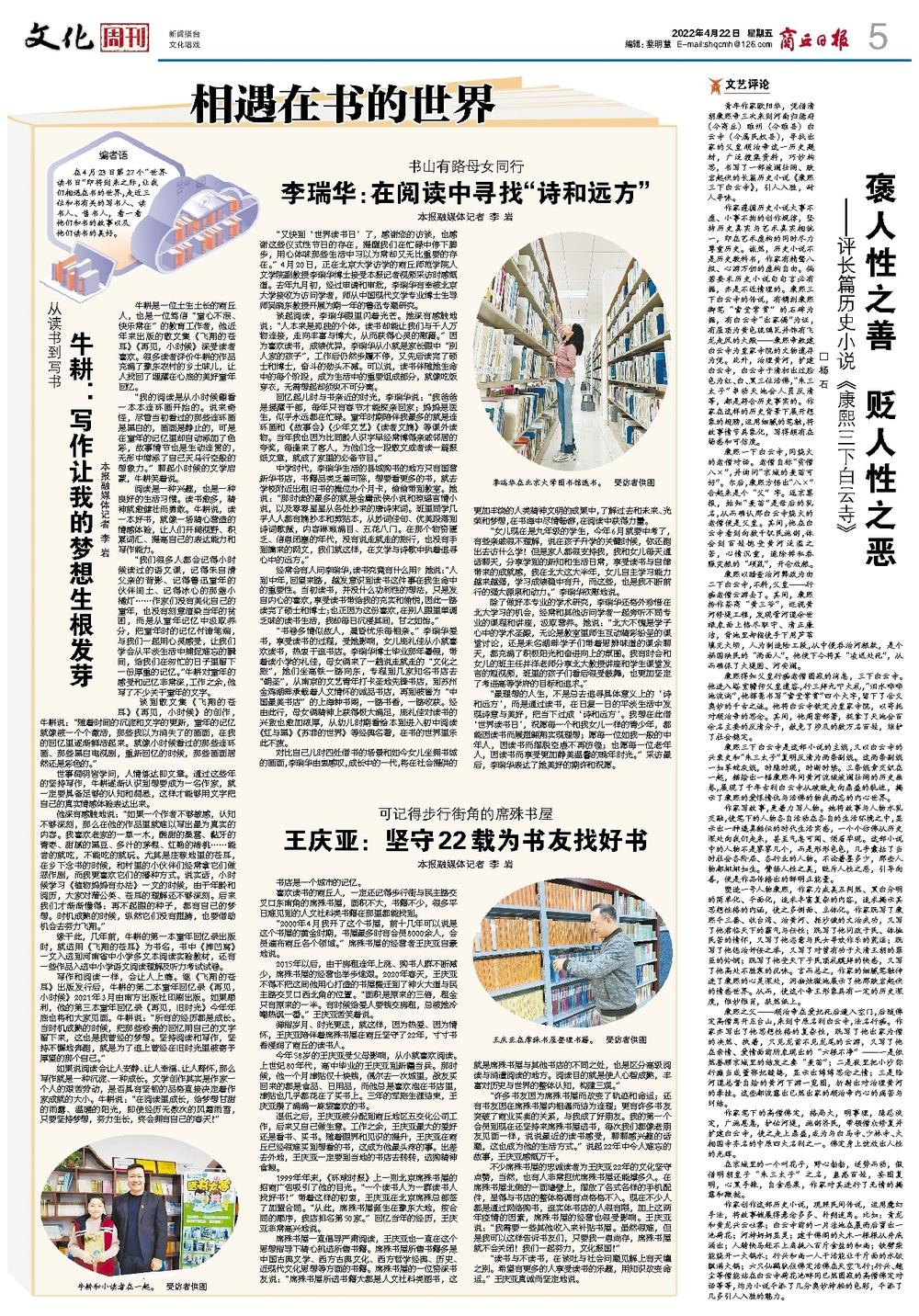青年作家欧阳华,凭借清朝康熙帝三次来到河南归德府(今商丘)睢州(今睢县)白云寺(今属民权县),寻找出家的父皇顺治帝这一历史题材,广泛搜集资料,巧妙构思,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、跌宕起伏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康熙三下白云寺》,引人入胜,耐人寻味。
作家遵循历史小说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的创作规律,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,即在艺术虚构的同时尽力尊重历史。诚然,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,作家有精骛八极、心游万仞的虚构自由。倘若要求历史小说句句言必有据,亦是不近情理的。康熙三下白云寺的传说,有镌刻康熙御笔“當堂常賞”的石碑为据,有白云寺“出家偈”为证,有屋顶为黄色琉璃瓦并饰有飞龙走凤的大殿——康熙帝敕建白云寺为皇家寺院的文物遗存为凭。此外,治理黄河,扩建白云寺,白云寺于清初出过脸色为红、白、黑三位活佛,“朱三太子”串动天地会人员反清等,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作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想象的翅膀,运用细腻的笔触,将故事情节具象化,写得颇有在场感和可信度。
康熙一下白云寺,同烧火的老僧对话。老僧自称“贫僧八×”,并询问“京城的麦苗可好”。尔后,康熙方悟出“八×”合起来是个“父”字。返京禀报,始知“麦苗”是母后的乳名,从而确认那白云寺烧火的老僧便是父皇。其间,他在白云寺看到向数千饥民施粥,体会到百姓饱受黄河泛滥之苦,心情沉重,遂除掉私吞赈灾粮的“硕鼠”,开仓放粮。
康熙以暗查治河弊政为由二下白云寺,不料,父皇——行痴老僧云游去了。其间,康熙扮作茶商“黄三爷”,巡视黄河修堤工程,发现管河道余世禄表面上恪尽职守、清正廉洁,背地里却指使手下用芦苇填充大坝,人为制造险工段,从中侵吞治河粮款,是个祸国殃民的“两面人”。他便下令将其“凌迟处死”,从而确保了大堤固、河安澜。
康熙得知父皇行痴老僧圆寂的消息,三下白云寺。他进入塔室瞻仰父皇遗容,行三拜九叩大礼,“泪水哗哗地流淌”,他挥毫书写“當堂常賞”四个大字,留下了含义奥妙的千古之谜。他将白云寺钦定为皇家寺院,以寄托对顺治帝的思念。其间,他周密部署,捉拿了天地会百余名主要的反清分子,赦免了涉及的数万名百姓,维护了社会稳定。
康熙三下白云寺是这部小说的主线,又以白云寺的兴衰史和“朱三太子”复明反清为两条副线。这两条副线一如草蛇灰线,时隐时现,时断时续。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,描绘出一幅康熙年间黄河流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,展现了千年古刹白云寺从破败走向鼎盛的轨迹,揭示了康熙的爱恨情仇与活佛的物我两忘的内心世界。
作家写故事,更着力写人物。她将故事与人物水乳交融,使笔下的人物各自活动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之中,显示出一种逼真酷似的时代生活实感,一个个仿佛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,甚至气息可闻、须眉毕现。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寥寥几个,而是形形色色,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、各行业的人物。不论着墨多少,那些人物都栩栩如生。赞扬人性之美,贬斥人性之恶,引导向善,便是作品传播出的鲜明正能量。
塑造一号人物康熙,作家力戒美丑判然、黑白分明的简单化、平面化,追求丰富复杂的内容,追求揭示其思想性格的内涵,使之多侧面、立体化。作家既写了康熙平三番、收台湾、治黄河、拒沙俄的文治武功,又写了他君临天下的霸气与任性;既写了他问政于民、体恤民苦的情怀,又写了他恣意与民女寻欢作乐的荒淫;既写了他惩治奸佞之举,又写了对曾有功于大清王朝的罪臣的怜悯;既写了他受天下子民顶礼膜拜的快感,又写了他高处不胜寒的况味。言而总之,作家的细腻笔触伸进了康熙的心灵深处,洞幽烛微地展示了他那跌宕起伏的情感世界。从而,使这个帝王形象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,惟妙惟肖,跃然纸上。
康熙之父——顺治帝在爱妃死后遁入空门,后随佛定高僧离开五台山,来到中原名刹白云寺,法名行痴。作家亦写出了他思想性格的复杂性,既写了他出家为僧的决然、执着,只见龙首不见龙尾的云游,又写了他在亲情、爱情面前所表现出的“六根不净”——一是依然眷顾京城里的结发之妻“麦苗”;二是夜里把小沙弥行癫当成董鄂妃缱绻,显示出绵绵思念之情;三是给河道总督自绘的黄河下游一览图,折射出对治理黄河的牵挂。这些都流露出已然出家的顺治帝内心的痛苦与纠结。
作家笔下的高僧佛定,格局大,明事理,隐忍淡定,广施恩惠,护佑河堤,施粥济民,带领僧众修复并扩建白云寺,使之走上鼎盛,成为与白马寺、少林寺、大相国寺齐名的中原四大名刹之一。佛定身上绽放出人性的光辉。
在京城里的一个叫花子,野心勃勃,逆势而动,假借明朝皇子“朱三太子”之名,蛊惑百姓,妄图复明,心黑手辣,自食恶果,作家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。
作家创作这部历史小说,观照民间传说,运用魔幻手法,将故事铺展得悬念多多、扑朔迷离。比如:青龙和黄龙兴云吐雾;白云寺前的一片洼地在晨雨后冒出一池荷花;河神奶奶显灵;建千佛阁的大木一根根从井底涌出;人骑快马赶不上肩挑八百斤食盐的和尚;铁劈柴能烧开一大锅水;行兴和尚一人干活能让千斤面的水饺飘满大锅;六只仙鹤驮住佛定活佛在天空飞行;行兴、越尘等僧能站在白云寺荷花池畔同已然圆寂的高僧佛定对话等等,均为小说平添了几分奥妙神秘的色彩,平添了几多引人入胜的魅力。